 |  |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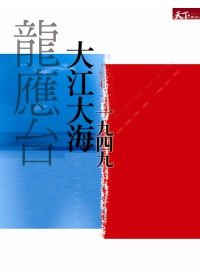 |
雪白血紅一書作者張正隆去年被捕『ML』
(中央社香港十二日電)此間「星島日報」今天報導,中共禁書「雪白血紅」作者張正隆已於去年底被捕。
報導說,張正隆是「瀋陽軍區」十四軍的中校,他搜集了大量文獻,並訪問了一些幹部,寫成了「雪白血紅」,披露國共內戰期間東北的實況。該書在一九八九年八月初版後翌日,即被禁售。
第一次看到這種狀況。不過,讀了「兵不血刃」這一章,如果他在當時被判死刑槍斃了(沒有發生),我都不意外。(1989年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,《雪白血紅》1989年8月在中國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)
長春和廣島,死亡人數大致相等。
廣島用九秒鐘。
長春是五個月。
百姓夾在中間
長春是在淪陷期間膨脹起來的城市。
“九•一八”後,日本集中國內一批一流專家,採用歐美式建設理論,到長春進行規劃設計。綠化系統,既吸收了霍德華的田園城市理論,又注意到整體環境。新區採用分流制的排水系統,以保持公園綠地流水清潔,利用天然溝渠造成借助於地形的綠化帶。主要幹道採用電力、電訊、照明線路地下化,新住宅區設置電力路線走廊。為適應三十年代城市交通方式,採用平面環狀交叉,設計了許多圓形廣場。
人口也由“九•一八”前的15萬,劇增到“八•一五”前的70萬左右。其中日本人為14萬。
長春圍困戰前,居民為50萬左右。(29)
5個月圍困,全城700餘萬平方米建築,230萬平方米被破壞。一切木質結構部分,大到房架,小到交通標誌牌,乃至瀝青路面,或用於修築工事,或充作燃料,而一切可以當做食物的東西,如樹皮、樹葉之類,都被盡情地送入口中,化作維繫呼吸運動的熱量。
戰後長春只剩下17萬人。
一是存有幻想,二是顧及軍心士氣面子,圍困之初,國民黨不准百姓離城。尚傳道提出“人人種地,日日練兵”,號召軍民同舟共濟,保衛長春。鄭洞國講臺灣正在訓練大批美械新軍,即將開赴東北大舉反攻,只要守住半年左右,大局能扭轉。
幻想成為空想,口號只是口號。即便人手一把鋤頭,掘去瀝青的馬路能長莊稼,也得等到秋後才能吃到嘴裡,而存糧只能吃到7月底。50萬張嘴,成了國民黨的沉重負擔。
7月下旬,蔣介石致電鄭洞國,從8月1日起,疏散長春哨卡內人口,只准出卡,不准再進。
共產黨早已森嚴壁壘。6月28日,1兵團政委蕭華在圍城政工會議上說:
「敵人疏散人口的方法,可能有以下幾種:一、強迫逼出,二、組織群眾向我請願,三、搞抬價政策,收買存糧,逼得群眾無法生活不能不外逃,四、出擊護送群眾出境。因次我對長春外出人員一律阻止,但不能打罵群眾,縱有個別快餓死者須要處理時,也要由團負責,但不應為一般部隊執行,更不能成為圍城部隊的思想。」(30)。
8月17日,1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際,在圍城部隊高幹會議上的報告中說:
「在圍城時期,基本上還是執行圍困封鎖,禁止人民與長春市之來往,禁止與長春之貿易關係。但在我警戒線附近,因蔣匪之搶掠驅逐與強制疏散而奄奄待斃之饑民很多,死亡率很大。這些人已經不可能回到長春市內增加敵人之負擔,故我們還是必須加以救濟。這對我們的政治影響及部隊的影響是很大的。關於放出與救濟這些難民有以下幾個原則:」
「甲、難民已進入警戒線內及警戒線外附近之地區,或我軍攻佔之地區,對是饑餓死亡很嚴重者,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濟,至於城內及敵乘隙新疏散出來之難民則暫不能救濟,待調查之後聽候處理,對於尚存有糧食,或將存糧出賣者不予放出。」
「乙、不是大肆號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,而是在部分地區(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)採取部分的放行,故可先派工作人員進入難民地區進行調查,將真正的難民予以組織,告以放行之時間地點,並予以證明,每一期預計放行之數目要先期報告,以便準備救濟。」
「丙、在放出之難民中,工人與學生可以吸收者經難民處理委員會轉至適當地點收容,但不是號召城內工人學生都出來。對於真正有特殊技術之人才,可以號召爭取其出來,亦送委員會。」(31)。
9月9日,“林羅劉譚”在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:
「我之對策主要禁止通行,第一線上五十米設一哨兵,並有鐵絲網壕溝,嚴密結合部,消滅間隙,不讓難民出來,出來者勸阻回去。此法初期有效,但後來饑餓情況愈來愈嚴重,饑民變乘夜或與白晝大批蜂擁而出,經我趕回後,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,由此餓斃者甚多,僅城東八裡堡一帶,死亡即約兩千。八月初經我部分放出,三天內共收兩萬餘,但城內難民,立即又被疏散出數萬,這一真空地帶又被塞滿。此時市內高粱價由七百萬跌為五百萬,經再度封鎖又回漲,很快升至一千萬。故在封鎖鬥爭中,必須採取基本禁止出入,已經出來者可酌量分批陸續放出,但不可作一次與大量放出,使敵不能於短期內達成迅速疏散。如全不放出,則餓死者太多,影響亦不好。」
「(二)不讓饑民出城,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,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,都是很費解釋的。饑民們對我會表不滿,怨言特多說:“八路見死不救”。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,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,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。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,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,說是“上級命令我也無法”。更有將難民偷放過去的。經糾正後,又發現了另一偏向,即打罵捆綁以致開槍射擊難民,致引起死亡(打死打傷者尚無統計)。」(32)。
比之草民百姓的命運,人世間的一切苦難都黯然失色了!
白骨之城
“兵不血刃”的長春之戰,把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推上第一線。
尚傳道在回憶錄中寫道:“根據人民政府進城後確實統計,由於國民黨‘殺民’政策餓、病而死的長春市民共達十二萬人。”(33)
10月24 日,南京《中央日報》在一篇《長春國軍防守經過》中寫道:“據最低的估計,長春四周匪軍前線野地裡,從六月末到十月初,四個月中,前後堆積男女老少屍骨不下15萬具。”
長春變成不折不扣的死城,餓俘之城,白骨之城!
天塌了
67歲的宋占林老人,離休前是長春市二道河子區城建局環衛科長。
老人說:「1948年春節前後,吉林和周圍城鎮有錢人都往長春跑,中農也跑,大車、爬犁絡繹不絕。國民黨宣傳共產黨“共產共妻”,“流血鬥爭”,都害怕。長春一下子就變擠了,住房緊張,煤柴緊張。穀草最貴,一斤穀草換幾斤大豆。跑進城的難民都有馬。那時糧食還不見緊張,大豆有的是,都用豆餅、大豆燒火做飯。我家也是,鍋上鍋下都是糧食。天化時就不大行了。先是把黃豆磨成麵吃,不消化,胃受不了。難民殺馬,烤馬肉吃,像現在街上烤羊肉串兒似的。最先餓死的不少是難民,和進城謀生計的手藝人」。
「我就這二道河子生人。父母,弟兄四人,四個妯娌,三個孩子。我們兄弟身強力壯,我和大哥是木匠,二哥是銅匠,在貧民區中算中上等人家。就這樣,13口之家也死了4口:父親叫流彈打死了,孩子全餓死了」。
朝陽區東朝陽路9居民委員會主任李素娥老人說:「那時,我家住在老虎公園(今動植物園)北門。一家8口,父母和6個孩子,我是老大,那年16歲。父親在南嶺運動場畫跑道圈,原來就病厭厭的,最先餓倒的,接著是大弟弟。男人不經折騰,女人抗勁兒。我們家全靠我折騰了。爹媽常說:是素娥救了一家人哪!」
「我們7月中旬斷糧,吃野菜、樹皮。先扒榆樹皮,扒掉老皮要裡面那層嫩的,粘粘乎乎挺好吃。後來甚麽樹都扒,老皮也吃。長春樹多,夏天馬路上 不見陽光,都是蔭涼。都扒光了,白花花的。」
「我有個二姨叔叔,在“60熊”一個特務連做飯。偽滿時,爹媽賣隻200多斤渚,給他娶的媳婦。媽說:3年大旱餓不死廚子,你去看看能幫點不。進屋就見鍋裡煮著大米飯,二嬸拿鍋蓋就蓋上了。二叔說:你吃一碗吧。我恨不能把頭都拱進鍋裡,一想到爹媽和弟妹,就說給兩碗我拿家去吧。二嬸臉不是臉,鼻子不是鼻子,說我們今晚就揭不開鍋了,還給你拿家去?我媽哭著說:這年頭沒親戚啦!」
「我家房後有塊地,頭年種點穀子,吃了些,裝了三枕頭。藏著掖著,尋思不到快餓死時不能動。鄰居有兩個姑娘和國民黨不正經,不知怎麽叫她們知道了,來幾個“60熊”,硬給搶走了。一家人哭啊。爹說:這是命,遇上小人了!」
「說到頭,還是空投大米救的命。」
「得拿命換。」
「老虎公園是個空投點,飛機一來就掉糧袋。盡是大米,南方大米,東北人叫“綫米”。飛機一響,國民黨就戒嚴。看不住。老百姓早準備好了,哪兒都藏人,空投也不都那麽準。老百姓搶,國民黨就開槍。開槍也搶,用小刀劃開袋子,摟些就跑。有的見到糧食就往嘴裡抓,甚麽部不顧了,也忘了,槍打刀扎,就那麽抱著糧袋不放,槍打死的,人踩死的,每天都有。我們家人祖祖輩輩都膽小,可人到了那份上也就沒甚麽膽小膽大的了。媽甚麽也捨不得吃,總讓我吃個半飽, 說你是咱家頂樑柱呀。我哪吃得下呀?走路打晃,動一動就冒虛汗,可一看糧袋掉下來,勁就來了。白花花的大米撈在手裡,那是全家人的命呀!」
「有個姓劉的姑娘,比我大一歲,叫糧袋砸死了。離我不到10米遠,砸得扁扁乎乎的。」
朝陽區義和路居民張淑琴老人說:「一天,我坐在炕上哄孩子,喀嚓一聲,一袋糧食掉下來。還沒明白怎麽回事兒,吵兒巴火進來幾個國民黨,都是新7軍的。魂兒都嚇飛了,沒聽見他們問甚麽。翻一大陣子,糧袋砸穿房蓋掉在天棚上了,正在我們娘們孩子頭頂上。是炒黃豆。他們就罵,說吃黃豆拉稀腸子都快拉出來了,大老遠的還送這破玩藝兒,嘴裡這麽罵,那眼睛瞪得“大眼賊”似的,掉進牆裡的也摳出來。」
「國民黨有搜糧隊,一斤半斤也拿走。我們家來過一次,翻得碗朝天,瓢朝地,用鐵釘子往地下捅。」
「有天來個兵,翻出幾個大餅子。我哪能撕巴過他呀,就說:你看看我那孩子吧,小貓小狗也給留條小命吧!他還有點良心,給留下兩個。」
「那年我25歲,3個孩子,大的6歲,小的1歲。唉,哪還叫孩子呀,猴啥樣他們啥樣。小女兒就那麽餓死了。吃奶孩子沒聽說有活過來的。再困個把月,就全完了。」
李素娥:「拿命換點大米不敢吃,拿去換糠、麴子、酒糟甚麽的,讓全家人糊口,搶大米不能拿麵袋,得用筐,不顯眼。後來筐也不行了,就穿個大布衫子,裡面縫些兜。去市場賣大米也一樣,一次叫幾個“60熊”發現了,說我是“大米販子”。就2斤大米。我抱住不放,在地上打滾。他們拽我去督察處,我不知道他們怎叫“60熊”,也不明白這“督察處”是幹甚麽的。旁邊人說:你就捨了吧,去督察處就沒命了。一個同學見了,跑回去報信。爹媽來了,給他們磕頭,一口一個 “長官”,“老總”,說孩子小,不懂事,高抬貴手開開恩。有個兵是遼南人,我們老家也是遼南,聽出是老鄉,就說到他們家看看再說,5個弟妹一水水躺在炕上,有出氣沒進氣樣兒。沒說甚麽,把那2斤大米拿走了。身上打得青一塊、紫一塊的,爹媽抱著我哭。」
「有一次賣大餅子,穀子、樹皮和麴子做的。想賣點錢,最好是換點藥,給爹和弟弟治病。吃點飯立刻就精神了,那算甚麽病呀?可人就是那麽怪。媽說,你上街還不叫人撕碎了呀!那時賣吃的,一個人賣,幾個人看著。怕搶。不少賣大餅子的,把命都搭上了,我出門沒走多遠就讓人搶了,邊跑邊吃。我追上個死人幌子樣的人,他已經吃光了。我蹲在那兒哭,他傻乎乎地看著我,站那兒也不跑了。」
「現在這人認錢。假藥,假種子,假化肥,甚麽都摻假,要錢不要良心。我們這茬人講名聲,講信用,講仁義。可他搶我大餅子,我搶國民黨大米,就是沒了禮義廉恥嗎?弟妹們吃東西我都不大敢看,一看心裡就癢癢,嗓子眼恨不能伸出個小巴掌。一些人是看見吃的,身不由己就上去搶了。」
「有人給我保媒。甚麽“保媒”,“結婚”的,就是換大餅子。和我大小的姑娘,不少都換了大餅子,換給郊區農民。孟家屯,就是現在第一汽車廠那兒,不管多大年紀,還是瞎子、瘸子,光棍都娶的小媳婦。我在電車公司工作時,幾個師傅都是小媳婦。」
「東西不值錢,錢不值錢,金子不值錢,人不值錢,幾個大餅子就領走一個大姑娘——就認吃的。」
宋占林:「剛解放時我當街道幹部,沒少處理這類離婚案。結婚為口飯,有飯吃馬上不幹了。政府政策是能過就過,不能過不硬捏。長春藥廠一個女的,有孩子了,非離婚不可,男的不幹,丈母娘說幾句不中聽的,就把丈母娘殺了。」
李素娥:「每天都餓死人。死在家裡的不知道,路邊越來越多。我在南關永安僑頭賣大米,身後咕呼一聲,一個老頭就倒那兒了。灌口米湯就能活過來。有收屍隊,一路撿,往車上扔,說“喂狗”。狗吃人,人吃狗,那狗才肥呢。」
宋占林:「死人最多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。洪熙街甚麽樣子沒見到,二道河子十室九空。」
「開頭還弄口棺材,接著是大櫃、炕席甚麽的,後來就那麽往外拖。也沒人幫忙了。都死,誰幫誰?拖不動了,就算到地方了。有人拖不動了,坐那兒就動不了了,也死那兒了,最後也沒人拖了。炕上,地下,門口,路邊,都是。有的白花花剩副骨架,有的正爛著,剛死的還像個好人。大夏天,那綠豆蠅呀,那蛆呀,那味兒呀。後來聽城外人說,一颳風,10裡、8裡外都薰得頭痛。」
「我們家附近沒一家不死人的。同院的王青山,5口剩1口。西邊何東山,也是5口剩1口。前院一個姓曾的木匠,7口人剩個老伴。“楊小個子”一家6口,剩個媳婦。後邊一家“老毯兒”(東北稱闖關東的河北人為“老毯兒”),6口全死了。」
「舊曆8月初,我臨出哨卡走到現在膠合板廠那兒,想喝點水:一家門窗全開著,進去一看,10多口人全死了,炕上地下,橫躺豎臥。炕上有的還枕著枕頭,女的摟著孩子,像睡著了似的。牆上一隻掛鍾,還“嘀滴答嗒”走著。」
「開頭見死人掉眼淚,頭皮發炸。後來也害怕,不是怕死人,是覺得自己早晚也是這條道。再往後見了打個唉聲就過去了,再住後連個唉聲也不打了,也不把死當回事兒了。」
「解放後,熟人見面就問:你家剩幾口?就像現在問:你吃飯了嗎?」
「解放後第一件事就是“救生埋死”。“救生”就是給活著的發糧食,“埋死”就是埋死人。我參加“埋死”了。幹一天給5斤高粱米,幹了個把月。全城都幹,全民大搞衛生運動,不然發生瘟疫更了不得。挖個大坑,把鋼軌甚麽的架上,屍體放在上面燒。大部分是埋的。有的集中一起挖個大坑埋,有的隨處挖坑就埋了。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爛炕上了,拿不成個了,唉,別說了。第二年看吧,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長草,那地太“肥”了。」
吉林省軍區原參謀長劉悌,當時是獨8師1團參謀長。老人說:「獨8師當時就在二道河子執行圍困任務。通信員說有個老太大,把餓死的老頭的大腿煮吃了,吃了也死了。團長吳子玉是個老軍,說哪能有這種事。通信員說,不信我領你去看看。進去一看,鍋裡還剩條大腿。團長回來跟我說,那天都沒吃飯。」
宋占林:「我出哨卡前,看到路邊一個人兩條大腿都剔光了。早就聽說有吃人肉的,還不大信。那肉是刀剔的,不是狗啃的。那時早見不到狗了。」
「1955年,我當區機關黨委書記時,有個挺好的黨員發展物象,向黨交心,說他那時吃過人肉。那還能入黨嗎?」
「最叫人揪心的是孩子。」
「不少人都把孩子扔了,扔到馬路邊上,希望有錢人能抱走撿條命。現在的東盛小學,當年就是學校,二道河子這片那兒最多。大都是5歲上下,有的拉拉巴巴剛會走,張著小手“媽呀”、“媽呀”叫,爬到馬路上的,爬進學校的,那個小樣呀!叫不動了,就歪在那裡,慢慢就死了,活著的還在那兒爬,啞著嗓子叫“媽”。人們都不敢往那兒去。每天都有送的,聽說真有叫人抱走的。」
張淑琴:「我在吉林大路那兒見過,披個小被,在那兒哭得泥人兒似的。看一眼趕緊跑,自己孩子都餓死了,抱回來不也是個死嗎?」
65歲的于連潤老人,退休前是朝陽區孔雀理髮社工人。老人說:「二道路那兒扔些小孩,一場大雨全淋死了,小肚子灌得鼓鼓的。唉,別說這個了,一說這個就想起我那死去的孩子。真作孽呀!」
「我那時候就理髮。餓得那樣,也有人理髮。甚麽人那時候還能想著理髮呢?」
「有錢人到甚麽時候都有錢,餓死的都是窮人。」
張淑琴:「新7軍的官太太穿旗袍,抹口杠,坐人力車,後邊跟好幾個護兵,有的軍官挎兩個太太壓馬路。人和人不一樣。」
「永春路的“老藏生”食品店一直營業。你想想,那掌櫃的會是甚麽人物?」
李素娥:「南關永安橋頭有家炸大果子的,那個香呀,一走到那兒就拔不動腳了。不要錢,用金銀首飾甚麽的換,那財發的呀!吃的都是當官的和有錢人,也沒見有人搶。一般人就是有油有麵,你炸個試試?」
宋占林:「逃進城的地主富農也餓不死,他們組織保安隊,老百姓叫“鬍子隊”。國民黨不發糧餉,吃穿全靠搶。搶還有名堂,今天這個“捐”,明天那個“稅”,可把地皮刮完了。」
于連潤:「那時咱就尋思呀,你國民黨和共產黨有仇,咱老百姓招誰惹誰了,要遭這種大難?可尋思這個有甚麽用,誰把咱草民百姓的命當命了……」
10月15日,鄭洞國的晚飯是四某一湯。
簫傳道說:“沒聽說有餓死士兵的事。”(34)。
“不給敵人一粒糧食一根草,把長春蔣軍困死在城裡!”
困死的都是百姓。
真空地帶
偽滿時期,日本人在城邊修了條環城公路,老百姓叫“圈道”。
圍城期間,這條圈道成了國共兩黨之間的真空地帶,老百姓叫“卡空”。
國民黨往外趕,共產黨往回堵,老百姓大都是夾在“卡空”裡餓死的。
高秀成老人的夫人譚文姝,當時是長春大學(現吉林大學)法律系學生。老人說:「長大早就停課了,門窗都沒了,桌椅砸壞了。學生分兩派,辯論,寫大字報,像“文化大革命”似的。國民黨特務動輒抓走進步學生,有的抓走就沒影了。我哪派也沒參加,像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逍遙派。」
「我是6月份出城,比較早。那時國民黨還不讓出城,老百姓大都未想到往外跑:我哥哥明著是國民黨長春市專員,實際是咱們的地下黨,當時我不知道。後來想,他大概知道圍城不是短時期的,所以讓我們趁早走。」
「天沒亮,就和姐姐、姐夫一家動身了。姐夫是市立醫院(今第二軍醫大學)內科醫生。同行的還有幾個醫生,都帶著家屬、孩子。約定在二道河子街頭集合,會齊了就走。我領著姐姐的大孩子,姐姐抱小的,姐夫背著東西。我甚麽也不明白,挺害怕,又覺得挺神秘的。國民黨卡子好像沒怎麽盤問,共產黨那邊有人接,都是我哥聯繫的,不敢走大路,就在草棵子裡蹚。草棵子裡有不少死人,把我嚇的呀,心“嘣嘣”直跳。」
朝陽區武裝部政委錢富永說:「外逃主要是三個口子:東邊二道河子,出去奔吉林;西邊洪熙街,奔公主嶺、瀋陽;再就是北邊的宋家窪子。我們家是從洪熙街附近出去的,番茄剛有點紅的時候。夜裡,黑黑的,從草棵子裡爬過去的。那時還不太嚴。」
宋占林:「我跑了三次,第一次是7月,出二道河子5裡路到靠山屯,天亮了,叫兒童團發現了。一看就明白是從城裡跑出來的。10多個小孩,管我要路條, 沒有就讓回去,可認真了。第二次想從卡子邊上溜過去,又給抓住了,不打不罵,反正怎麽商量也得回去。光有路條也不行,還得有老婆孩子。兩次都帶著老伴和孩子,若是我一個人非扣住不可。」
「開頭出不去還能回來。後來國民黨准出不准進,出不去就只有夾在“卡空”裡等死了。」
「那也跑。豁出去了。怎麽也是個死,往外跑還能有點指望。」
「我們家是分四批走的。弟弟和弟媳第一批,我第二,二哥和母親第三,母親走時大哥還在家守著。哥四個各奔它鄉。我和老伴在“卡空”裡待3天出去了。」
于連潤:「我們家在“卡空”待10多天才出去。」
「臨走買輛推車,把點破爛裝上。把點黃豆、糠、麴子都做成大餅子,帶上。頭道卡子是國民黨,挨個搜,不要錢要東西,貴重東西和吃的。人家有經驗,再裝,有錢人也能瞅出來。看我那樣兒,翻幾下一揮手讓走了。有錢的不行,不拿出好東西不讓過。」
「“卡空”裡那人哪,男男女女,老老少少,坐著的,躺著的,也分不清是死是活。瞅著那樣兒,腳下就有點軟了。咬咬牙,硬看頭皮,還是闖。」
「“卡空”裡“鬍子”多,搶吃的。一口井他們霸著,怕老百姓給喝光了。莊稼地也霸著,誰也不准進,白天晚上打槍。我有個侄女婿不聽邪,也是餓急眼了,晚上想弄點毛豆,去了再沒回來,人們擼樹葉子吃,成牲口了。樹沒皮沒葉,草剩個杆,有的地方杆也不多了。嘴都吃綠了,人都吃綠了。」
「一家一堆,擠擠匝匝的。有的偎在破房茬子裡,大部在露天地待著,鍋呀,盆呀,車子,被子,活人,死人,到處都是。8月,正是最熱的時候, 日頭那個毒呀。突然下起大雨,活的淋得像塌窩雞崽子,死的泡得白白胖件,就那麽放著爛著,骨頭白花花的,有的還枕個枕頭,骨架子一點兒不亂。」
「人餓了,開頭腳沒根,渾身直突突,冒虛汗。餓過勁了就不覺餓了,暈暈乎乎,飄飄悠悠,像騰雲駕霧似的,不覺得難受了,也不怎麽想吃甚麽了。 可一看到能吃的東西,立刻就想吃,就想搶,不少死人身邊都光溜溜的,一根草都沒有。能說話時,一聲又一聲聽不出個個數,一聲聲都像是“餓呀”、“餓呀”。 沒聲了,眼睛有時還睜著,望天望地,半天不眨一下,甚麽表情也沒有。慢慢地,眼睛再也不睜了,還喘氣兒,像睡著了,這就快了。快了也能挺個一天兩天的,人命可大了,像燈油不熬乾不死。有的瞅著還像笑模悠悠的,更嚇人。」
「趕上毒日頭,那人一天功夫就發起來了。腦袋有斗大,屁股像小鼓似的,眼瞅著發,先綠後黑。一會兒“啪”的一聲,又悶又響,肚子爆了。白天晚上都響,夜靜聽得最清。這一聲,那一聲,有的就在身邊響,鼻子早就聞不出甚麽了,可那一聲響過後還是受不了,沒聞過的想像不出那味兒。」
「在“卡空”裡熬過10天的人不多。老天爺照應,那幾個大餅子過卡子沒翻去,“鬍子”也沒搶去。不能讓誰看見,天黑時偷偷掰點吃。這麽對付有10天,又吃兩天草和樹葉子。渴了喝雨水,用鍋碗瓢盆接的。這些喝光了,就喝死人腦瓜殼裡的,都是蛆。」
「就這麽熬著,盼著,盼開卡子放人。就那麽幾步遠,就那麽瞅著,等人家一句話放生,卡子上天天宣傳,說誰有槍就放誰出去。真有有槍的,真放,交上去就放人。每天都有,都是有錢人,在城裡買了準備好的,都是手槍。咱不知道。就是知道,哪有錢買呀!」
張淑琴:「我們在卡子前排隊,推車一個接一個,八路在隊伍兩邊來回走。邊走邊說:誰有愴、子彈、照相機,交出來就開路條出卡子。老百姓吵吵嚷嚷的,說甚麽的都有——那些話呀,說不得……」
「平時在“卡空”裡都不吱聲。兩邊便衣挺多,還有“鬍子”。那時那人都老實,怎麽擺弄怎麽是,像小貓似的。也是餓的沒精神,不想說了。」
「我們家是9月16號那天走的,在“卡空”待一宿就出去了。是托了我老伴的福。他是市立醫院X光醫生,那邊缺醫生,講明白就讓過去了,挺痛快。不知道有這條,不然早走了。」
宋占林:「我運氣也挺好。在“卡空”裡待兩天,碰上個小時候在一起撒尿和泥玩的夥伴,小名叫“來順”,姓王,前街的:他當八路了在卡哨上,挎個木頭匣子槍進來偵察。他問我他家人怎樣了,我說全沒了。他蹲那兒就哭,嗚嗚的。哭一陣子,我說你看我和你嫂子怎麽辦哪?他抽抽嗒嗒地說有命令,你們這片不放,明天放“馬車地號”的,你跟他們走。“馬車地號”都是趕車拉腳的人,叫這麽個名字。若不碰上他,八成沒今天了。」
于連潤:「我是一沒熟人,二哪也不缺個剃頭匠,甚麽門也沒有,只有硬挺乾熬。一塊兒來的不少都完蛋了,我也快不行了,就準備讓人聽個響臭塊地了,發了個救命的“難民證”(35)。這個謝天謝地呀,出去沒幾天又回來了——長春解放了。」
「出哨卡就有吃的。稀粥,麵不麵,楂子不楂子,一人一大碗。不能吃乾的,胃受不了,有人喝光了還要,不給就搶,撐死了。」
李素娥:「我有個舅舅,還有個姨姨和姨丈,都是出卡子後撐死的。」
「我們家也準備出去了,推車甚麽的都準備好了,第二天天剛亮,爹說素娥你快起來,這槍口怎麽都對上咱們了?我一看,可不是怎麽的。我說國民黨要殺人了。爹說:不對,有變。後來才知道,“60熊”起義了。」
「八路進城就發糧,大車呼呼朝城裡運。我去扛回40斤。別看走路都打晃,再給40斤也能扛回來。飯做好了,媽還捨不得吃。我說這日子過去了,共產黨來了就好了。媽捧著飯碗,眼淚劈里啪啦往下掉,說:老天爺呀,可算活過來啦!」
1987年,美國德州一所保健學院的教授,對43萬2千人的死亡時刻進行數理統計,發現死亡率最高的時刻,為每天淩昊4時至7時。
對於廣島,死亡率最高的時刻,無疑是1945年8月6日。
對於血城四平,死亡率最高的時刻,是1947年7月14日至26日。
對於死城長春,死亡率最高的時刻,是1948年5月至10月。
一座城市,因戰爭而活活餓死這麽多人,古今中外,絕無僅有!
歷史如是說
當戰爭以鐵與火與血的方式,在四平,在錦州,在遼西吼嘯、撲打時,從綠春到金秋,長春150個黎明和黃昏靜靜悄悄。
於是,關於這場圍困戰的文章,幾乎都寫著“兵不血刃”四個字。
當暫52師師長李嵩弟弟的妻子被送進城去,接著又送去失散的孩子,闔家團圓時,草民百姓開始家破人亡,一個個嬰兒被扔到街頭號泣。當60軍副官處長張維鵬等人的妻子兒女,被優待送出哨卡,並在沿途受到關照時,沒有槍和照相機的芸芸眾生伴著壘壘白骨,成群結隊地跪在哨卡前,苦苦哀求放生救命。
這就是:“兵不血刃”!
孫子說:“是故百戰百勝,非善之善也;不戰而屈人之兵,善之善者也。”
不戰而屈10萬守軍,實為“善之善者也”。可對於草民百姓的遍地餓俘和白骨呢?瞬間的屠殺與慢慢地餓斃,其間有殘忍與人道之分嗎?
血肉橫飛也好,兵不血刃也好,任何形式的死對於生命本身都是相同的。而同是生命的消亡,唐山大地震,南京大屠殺,長春圍困戰,自然界的災難與人類的殺戮,侵略者的屠刀與骨肉同胞的相殘,是一樣的嗎?
那位挎支木頭匣子槍的圍城的“來順”,一家人不也就剩他一個了嗎?
流血的政治演化成這種不流血的政治,那就是最殘酷、最野蠻的戰爭了!
長春一些老人說:打記事起,我們這疙瘩就沒得好過。“小鼻子”欺負咱,“大鼻子”糟害咱,“小鼻子”才狠呢,“大鼻子”才壞呢。好歹把這些畜牲盼走了,折騰得更厲害!外國人不把咱中國人當人,中國人怎麽也不把咱老百姓當人呢?
當年參加圍城的一些老人說:在外邊就聽說城裡餓死多少人,還不覺怎麽的。從死人堆裡爬出多少回了,見多了,心腸硬了,不在乎了。(有的老人說:那時候那人好像已經不知道甚麽叫“驚訝”了。)可進城一看那樣子就震驚了,不少人就流淚了。很多幹部戰士說:咱們是為窮人打天下的,餓死這麽多人有幾個富人?有國民黨嗎?不都是窮人嗎?
沒參加圍城的部隊,看到出來的難民人不人、鬼不鬼的樣子,也這麽說,這麽想。
圍城初期,有人在圍城政工會上講:“要將老百姓的饑餓貧困的罪過歸到敵軍及敵政府身上,擴大他們與群眾的矛盾,孤立敵人。”(36)。
後來的回憶錄,對此或避而不談,或一筆帶過:“當然,長時間圍城,也給城市人民帶來一些苦難,”(37)。
有人說:活活餓死那麽多人,太“那個”了,不好說呀!
如今一個人質,會把首相、總理、總統折騰得寢食不安,使出渾身解數,通過各種途徑進行斡旋,解救。這充份顯示了一個民族和人類的人道、人權、尊嚴、價值和文明進步的自主意識。當此稿正修改到這裡時,被困在阿拉斯加海冰區的三條倒楣的灰鯨,成了人類的寵兒:世界上最大的“星系C5型”軍用飛機被調往那裡,一條大型破冰船為它們開出條8公里長的水道,兩架“天鶴”式直升飛機整天在上空盤旋,花費達數百萬美元。其實,這種從1946年起受保護的灰鯨,由於數量驟增,10年前已經允許適量捕殺了。
若說講這些太遠了,電影《莫斯科保衛戰》中有個鏡頭挺近的:當一座城市(名字記不得了)被德軍包圍,紅軍準備血戰到底時,指揮員命令老人和婦女、兒童:為了俄羅斯,你們立即出城向敵人投降!
在“兵不血刃”的長春,誰應對無辜百姓的壘壘白骨負罪呢?
歷史說:這是戰爭。戰爭就是人殺人,人吃人。為達目的,戰爭是不擇手段,不顧一切的。
歷史說:只要是戰爭,平民百姓遭難就是難免的,眼睜睜活活餓死這麽多人是太“那個”了,從這種聳人聽聞的殘酷、野蠻行徑中,正可以瞭解和透視中國歷史和這場戰爭的淵源、特色。
歷史說:歸根結底,是誰發動了這場內戰,他們為甚麽能夠發動起這場內戰,中國的老百姓為甚麽只能像羔羊一樣束手待斃?
歷史還問:如果再發生一場內戰,誰敢保證中國不會出現長春第二?
遼沈戰役前,戰爭中軍民比例是二兵一夫。
遼沈戰役期間,直接用於支援前線的民工達160萬人,一兵二夫。
錦州戰事正烈,廖耀湘兵團攻佔彰武,將後方補給線切斷,前方糧草。彈藥和被裝供應不上,特別是油料短缺,汽車大部停駛,遼西和熱河人民,人背馬馱駱駝運,將油料送到前線。又從奈曼旗到北票,日夜搶修出一條700多里的公路,基本保證了前線供應。
黑山阻擊戰中,民工修工事,運彈藥,背傷患,送飯菜。一座不到萬人小縣城,出動130萬個工日。
3年內戰中,有多少民工倒在黑土地上?
僅一場黑山阻擊戰,就倒下400多人。
冬季攻勢和四保臨江、三下江南,雪白,血紅。最刺眼的,就是一具具穿黑棉襖的遺體。
推著車,挑著擔,抬著擔架的人民,直接投入戰爭,一直走到天津城下。
送走了兒子、丈夫和父親的父母、妻子和兒女們,再用扶犁握鋤的粗糙的手,支援這場戰爭。
長春則是50萬人民支援城外的10萬部隊——但他們不是“夫”。
他們沒有槍,算不得戰士,但是,被逼進死地,上天無路,入地無門的他們,搶空投大米,發動糧食戰,以人的強烈的求生欲望,“配合”城外,苦苦地進行著一場無形的封鎖與圍困。城裡多張嘴,國民黨就多一份壓力。城裡添具白骨,就多一顆射向國民黨軍心土氣的子彈。洞簫,殘月,家鄉小調,城外四面楚歌。城內,街頭風雨中號泣、倒斃的孩子,烈日下和靜夜中“蓬啪”炸裂的屍體,就是炸響在國民黨心頭的軟性原子彈。
沒有長春的纍纍白骨,有這座名城的“兵不血刃”嗎?
蔣介石的前妻毛福梅,是被日軍飛機炸死的。
共和國的旗幟上,染著毛澤東六位親人的血。
倒在這場內戰中的無辜百姓呢?長春這座死城的餓俘和白骨呢?他們是泰山?是鴻毛?還是像那滿山遍野的小草甚麽的?
那些三代橫屍炕上地下,門口街頭,斷了香烟的家庭。那些還未來得及看清這個世界是個甚麽模樣,就被扔到街頭的孩子。那些用青春換了大餅子的姑娘。那些被血一樣的高梁米粥撐死的人。那些吃人肉死掉了,或是不能入黨的人。被戰爭夾在中間,呼天不應,叫地不靈的草民,不才是最大的受難者和犧牲品嗎?
做為人來到這個世界上,他們的人格、尊嚴和感情,難道不應該同樣地受到珍視和尊重嗎?
美國人在華盛頓修了那麽多紀念睥,其中有座“越南戰爭紀念碑”,冷冰冰的黑色大理石上,密密麻麻地刻著那麽多姓名。那僅僅是在告誡人們,不要忘記在那場一無所獲,也與美國百姓毫無相關的戰爭中,倒在遙遠的南亞叢林中的美國軍人嗎?
(美國人的噩夢是“越戰”,中國人的噩夢是“文革”——早有人吵吵要建立一座“文革”博物館,不知道能不能和同時才能建起來。)
我們曾在黑土地上建了那麽多紀念碑,碑文寫了砸,砸了再寫。在雙城,在帽兒山,在牤牛屯,在許多與“東總”有關的地方,都曾籌建各種各樣的紀念碑和紀念館。有的地基打好了,有的文物收集得差不多了,有的已經快開館了,那個最大的“文物”256號三叉戟一聲響,一切都消聲匿跡了。
死城的累累白骨,應該避而不談,或是一筆帶過嗎?
為了這種亙古未有的慘絕人寰的悲劇,不再在我們的黑土地、黃土地和紅土地上重演。為了中國普通老百姓的權利、人格、尊嚴和價值,不再被漠視、踐踏。為了今天和明天的“小太陽”,能夠永遠在和平的陽光下生活。一句話,為了像今天唱的那樣,“讓世界充滿愛”,我們是不是應該在這片黑土地的白骨 之上,建一座碑?
那碑文是現成的。
注釋
(33)(34)《遼瀋戰役親歷記》,403、404頁。
(35)這個“難民證”,老人保存至今。
正面為:
難民證
茲有自長春逃出難民于連潤等4人,經審查後,准予分散謀生,沿途崗哨查驗放行為要。
年齡40 性別 男
住址長春二馬路8號 職業 商
分散地點苑家屯 縣 區 村
自 17 起
行程 9月 日
至 20 止
發糧黃豆4斤
長春難民處理委員會發(此處蓋有“長春難民處理委員會”公章)
民國三十七年9月1日
背面為:
難民紀津
1.在指定時間內,到達指定地點。
2.到指定地點後,向當地政府報告,並服從管理。
3.不得造謠生事及一切破壞行為,違者繳銷難民證,並予以處罰。
4.沿途不得偷竊食物,如包米土豆等,及一切擾亂社會秩序行為。
(36)長春市地方史誌編纂委員會(1987年),《長春黨史資料》第1輯,92 頁。
(37)1987年第1、2期《黨史資料研究》,26頁。
(《雪白血紅》頁467)
相關文章:
江山代有英雄出,各苦生靈數十年
為什麼不要跟人爭論政治、宗教議題?——我們先用情緒下決定,再用理性找理由
兵不血刃——王鼎鈞《關山奪路》中的長春圍城
兵不血刃——龍應台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中的長春圍城
兵不血刃——柏楊《倚夢閒話第八集,魚雁集》中的長春圍城
如何輕易地讓人道德沈淪?
電影「惡魔教室」(The Wave;Die Welle)




0 意見:
張貼留言